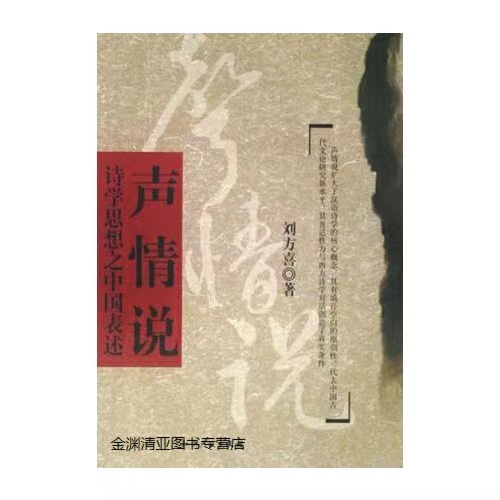
刘方喜的博士学位论文论题选择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“声情说”,那时答辩委员会认为论文很富创见,是篇优秀的博士论文。后来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继续深造,进一步完善这篇论文。两年之后,他的出站报告得到了鉴定小组专家们的一致好评:认为成绩优秀,就其创新意义来说,这一成果代表了当前古代文论研究的新水平。
刘方喜博士治学十分投入、认真,他没有把自己经营了好几年的成果匆匆地拿出去出版,而是又花了几年时间,对这篇研究报告不断进行充实与完善,达到了目前60余万字的规模,虽然不好说十年磨一剑,但他孜孜以求,确是显示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可贵精神。
那么这项研究所代表的新水平表现在什么地方?主要在于,作者在阅读大量古代文论典籍的基础之上,钩深致远,恢复并提出了汉语诗学中的 “声情说”,对它进行了科学的、独到的阐释,并把它提升到与古典诗学中的“意象”同等的地位,探究它们与另一重要范畴“神韵”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。“声情说”扩大了汉语诗学的核心概念,通过诗话之诗学与经学之诗学的融通,恢复了汉语诗学思想完整之格局,对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明。
作者说,我们古人高度重视汉语感性形式的人文创造,而汉语古典诗歌丰富的“意象”、灵动的“神韵”、茂美的“声情”,充分展示着与汉语不可剥离的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特征,我以为说得很对。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“声情说”虽有人不时提及,但是极少有学者就其原创性的丰富内涵、特别是它在汉语诗学结构中看来是不可或缺的地位,做过深入、系统的研究。“声情”这一概念的提升,对于古代诗学的深入研究具有原创意义。刘方喜博士将“声请说”视为“诗歌语言形式理论”,探讨了它的语言哲学基础,把诗学之“言不尽意”、“言之不足”确立为考察语言形式也即汉语诗学形式深层之“逻辑起点”,并强调从不同的“逻辑起点”出发,语言形式的创造在诗歌活动中就会产生不同的价值与地位。同时作者又将“声请说”视为一种“意义”的理论。确实,我国20世纪文化、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,外来的文化哲学、从科学主义发展到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影响十分严重。语言学重视声韵的研究,成就突出,但居主要地位的是技术上的文化处理;白话新诗后来虽然注意到了民族的风格特色,但同时却忽视了汉语诗学自身所蕴含的人文价值。在文学的意义、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,20世纪以来,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逻辑的影响,文学理论中常常把二者截然分开加以理解,文学形式成了一个盛放东西的容器。现象学美学、新批评等学派以及巴赫金等人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,提出了形式与内容在话语的层层递进、不断融合共生的形态中形成,而后成为作品整体的层次说,或是提出了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离的有内容的形式与有形式的内容说。但是声情说从我国古代思想源头与丰富资源之中,揭示了从诗歌实践的原始形态,就把诗歌意义、内容形式视为一体,展现了我国诗学元典并未将形式从内容剥离开来,或是剔骨还父式地将内容剥离于形式这一独特的视域、丰富的内涵与中国特色。“声情说”向我们揭示,文学创作不仅是情感的冲动,而且也是形式创造的需求,两者相互融合,天然璧合而共生一体。因此在这点上,可以说“声情说”对于中外诗学中多种理论的偏颇之处有所纠正,使创造的隐秘更接近真实,显示了我国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的重要特色。这样,“声请说”实际上表现为一开始就是形式与意义无形融合、共生的语言诗学。人文科学中一个概念的提出、发明与它的生命力,在于它是否按照其自身的学理提出来的,也即这一被提出的抽象化了的概念,能否反映被它概括了的复杂现象的真实性与实在性,它的历史的轨迹、现实的需求与发展的前景,以及它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,从而成为概念系统中一个组成部分。我以为“声请说”是符合这一要求的。
作者在这一论著中,提出了不少极富启迪意义、值得我们思考与吸取的观念。例如以往重视“意象”而轻“声情”,有“意象思维”之说而不知“声情思维”也是一种诗性思维,即那种表现为“语音形式结构的和谐合规律性”,它在诗人诗思的生成中发生着广泛的影响。从哲学元典寻找中国式的哲学存在论的儒道融合的人生图式、世界图式,即“未形—有形—无形”,在此基础上来探讨诗歌语言形式理论的价值,试图从一个方面,纵横贯通地对“意义”与“形式”作出“中国式解答”,对诗学思想进行“中国式的表述”。又如作者提出,在提升“声情”这一范畴时,也就揭示了一个系统,即汉语诗学范畴系统:声情、意象与神韵;揭示了两大序列,即“形式序列 ”的“未形-有形-无形”与“功能序列”的“不尽意—尽意—意无穷”,并在这两个序列的相互作用中,探讨诗歌的动态超越过程,儒道思想互补的诗学特征,等等。
《声请说》一书,立意深刻,构思独创,取材宏富,理论发明与实证阐发俱佳。它不仅恢复、深化了中国诗学的原有格局及其特征,而且注意到了它的普适性意义,并为与西方哲学、诗学的对话与互动,创造了真实的条件。
是为序。
(钱中文先生为本书所作《序》)

